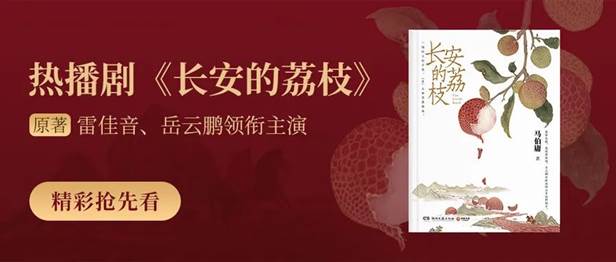
近日,改編自馬伯庸同名小說的電視劇《長安的荔枝》開播即火。由雷佳音飾演的九品小吏李善德蓬頭垢面奔波在嶺南與長安之間,只為完成那個“不可能的任務”——在荔枝變質前,將其從五千余里外的嶺南運至長安。
熒幕之外,馬伯庸原著小說再度引發閱讀熱潮。這本七萬字的中篇小說,以“一騎紅塵妃子笑”的詩句為引,在歷史的縫隙中編織出一則跨越千年的現代寓言。
當文字化為光影,原著與劇版各自綻放異彩,不變的是那枚小小荔枝背后,映照出的盛世真相與人性微光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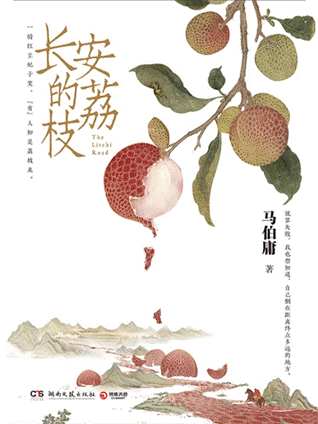

靈感起源:從杜牧詩句到歙縣文書
馬伯庸的創作常常源于歷史縫隙中的點滴線索。《長安的荔枝》的靈感最初源自杜牧“無人知是荔枝來”的詩句——他不禁發問:那顆跨越五千里的荔枝,究竟讓多少個“李善德”不堪重負?
而真正觸發創作靈感的,是他在研究《顯微鏡下的大明》時發現的一份徽州文書:明代歙縣人周德文因政治遷都被迫南遷的經歷,讓馬伯庸聯想到個體在歷史洪流中的無奈與掙扎。2020年5月,馬伯庸果斷放下其他工作,試著以周德文式的視角解讀“一騎紅塵妃子笑”,從動筆到寫完,恰好是十一天,和李善德的荔枝運送時間等同。
在原著中,李善德明算科出身、貸款買房所具有的現代性隱喻,以及官場中“忍氣吞聲科”的黑色幽默,都是馬伯庸對歷史與現實進行雙重解讀的體現。
影視突破:鄭平安帶來的雙線江湖
電視劇將原著7萬字內容擴充至35集,創作團隊面臨的首要挑戰是如何豐富敘事維度。劇版在保留李善德運送荔枝主線的基礎上,創造性地加入一條全新故事線——鄭平安的權謀暗戰。這個由岳云鵬飾演的小舅子,不僅與雷佳音飾演的李善德形成鮮明對比,更成為串聯權謀線索的關鍵環節。
在原著中,李善德獨自南下執行任務,而劇版通過賦予鄭平安臥底身份,將荔枝轉運與朝堂爭斗巧妙地結合在一起。鄭平安的世故與機智,與李善德的木訥與堅韌形成了強烈的戲劇沖突,岳云鵬的喜劇才能在此成為解構官場荒誕的有力武器,不僅緩解正劇的沉重氛圍,而且也意外揭示了職場生存的普遍法則。馬伯庸認為:“劇版的優勢在于能夠讓角色更加豐滿,彌補原著篇幅有限的遺憾,讓觀眾看到每一個角色完整的成長曲線。”
此外,劇版《長安的荔枝》延續了原著“大事不虛,小事不拘”的創作風格,在尊重歷史的基礎上巧妙演繹。主角李善德借貸“香積錢”買房,歷史上確有此制;楊貴妃六月一日的誕辰,取自晚唐袁郊《甘澤謠》;主角的名字則源于敦煌經卷所載武則天時代的“司農寺上林署令李善德”。這些精妙的細節,正是《長安的荔枝》洞見歷史的幽微光芒。
千年啟示:盛世齒輪下的個體覺醒
《長安的荔枝》的最大魅力在于它是一個跨越時空的生存寓言。李善德所面臨的困境——房貸壓力、職場中的精神控制、理想與現實的矛盾——在當代社會依然能引起人們的強烈共鳴。在原著中,他最終選擇前往嶺南流放,卻因妻女的陪伴而毫無怨言;而劇版將其妻子的結局改為病逝,增強了故事的悲情色彩,也引發了原著粉絲的爭議。
但無論改編如何,故事的核心始終不變:在絕境中堅守尊嚴的微光。李善德的“荔枝”,既是生存的憑借,也是對荒誕命運的溫和反抗。馬伯庸曾說:“一直以來我有一個很強烈的、堅定的史觀:所有的歷史都是由人民群眾創造的。這些人民群眾單一個體是無力的,也很容易被歷史長河湮滅掉他們的聲音。但是當千千萬萬個這樣的人聚合到一塊,他們形成的需求,就是所謂的時代之潮。” 這種對平凡人的理解與共情,正是《長安的荔枝》超越一般類型小說的關鍵所在。
熒幕上的《長安的荔枝》正熱播,而書頁間的沉思更值得品味:在宏大歷史的齒輪下,每個普通人的選擇,都決定著盛世的成色。看劇不過癮,還有馬伯庸其他作品一“讀”為快。
其他作品:
馬伯庸作品書單 | 在歷史的褶皺中,洞察永恒的人性
《風起隴西》


馬伯庸的首部長篇歷史懸疑小說,以三國時期諸葛亮北伐為背景,聚焦秘密情報戰線上的無名小人物,通過一場圍繞蜀漢弩機技術的諜戰陰謀,揭開歷史洪流中個體掙扎與權謀博弈的悲壯真相。
《長安十二時辰》


講述盛唐長安的生死危機,是馬伯庸首部成功影視化的代表性作品。
《顯微鏡下的大明》


從稅收糾紛到科舉舞弊等事件,展現底層文書如何挖掘歷史真相。
《兩京十五日》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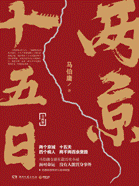

以《明史》為框架的奇幻之旅,堪稱明朝版的“極限挑戰”。
《食南之徒》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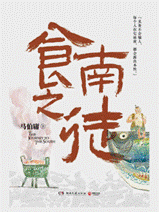

基于《史記》中“因一種食物滅國”的真實事件虛構,展現食物如何改變地理認知與國運。